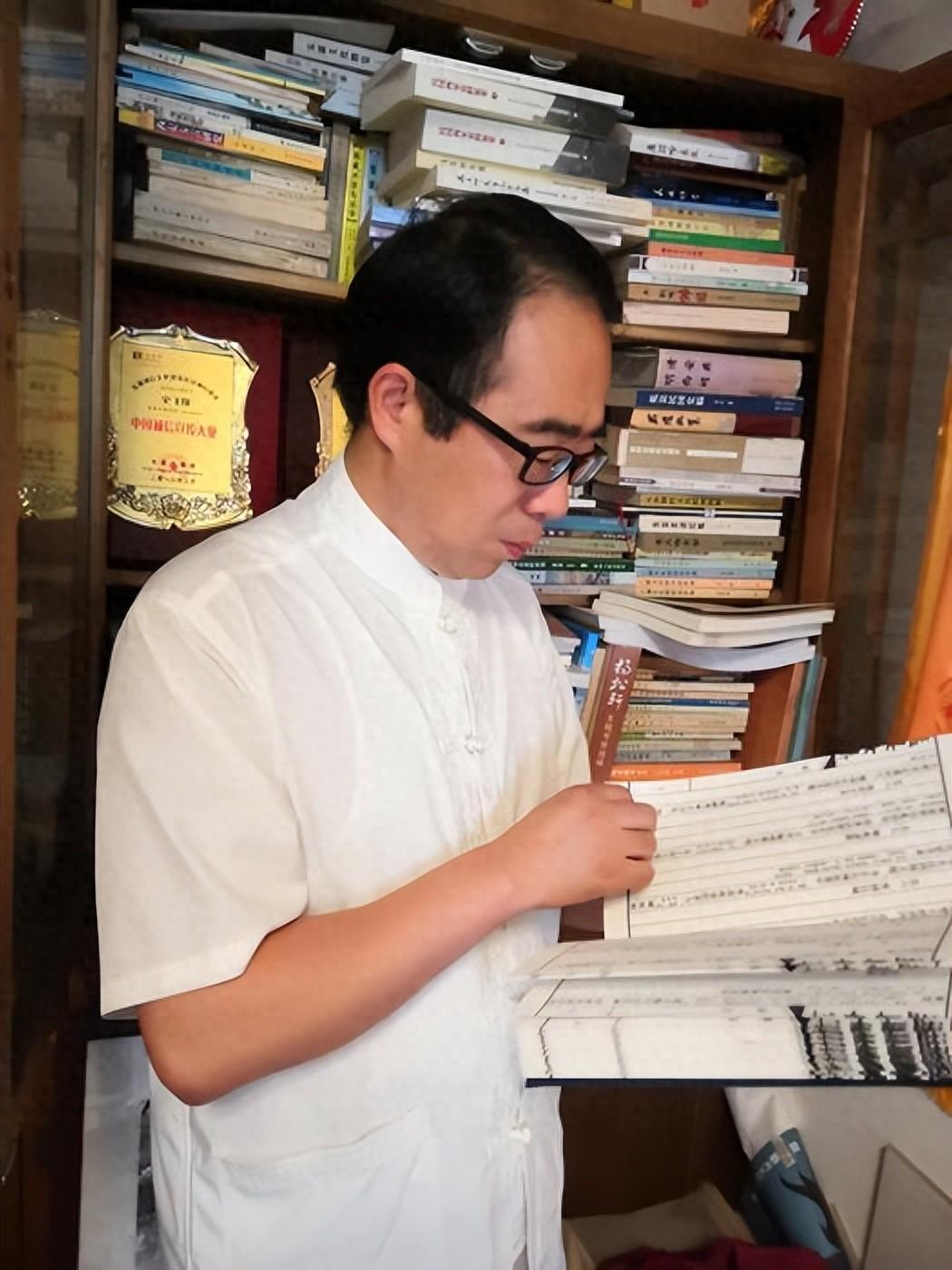殷鑫|麦黄杏
文/殷鑫 图/国风图库
麦梢一黄,杏儿也就黄了。

好些年没吃杏了,花几块钱买斤尝尝,酸酸、甜甜的,满口生津。不由又想起了外婆,想起了外婆家的麦黄杏。
外婆个头低矮,身板硬朗,是个干净、麻利、勤快的女人。出出进进风风火火,大老远就听得见咚咚响的脚步。不知何故,外婆的双眼总是红红的,眼角时常发炎,见风流泪,总不见好。
听母亲说,她们祖上算得上方大圆殷实之家,但经不起外祖父一根烟锅日夜不息地冒烟,竟把个好端端的家烧得日渐衰微,把自身抽得骨瘦如柴,五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因而,外婆自出嫁就没享过几天福分,倒是后院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杏树给外婆带来不少开心与快乐。
暖暖的春风一吹,杏花就开了。白白、粉粉的,看着蜜蜂、蝴蝶上下翻飞,闻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心儿都醉了。
一年一度的杏花雨下过,杏儿在树叶间悄悄地孕育,外婆就会自言自语:”杏儿杏儿快长成,让我外孙解馋虫。”我也就开始昼思夜盼地想那麦黄杏了。
外婆疼爱我,每次到家,她都会从屋梁上挂着的笼子里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见我有时实在想吃杏,外婆会用竹竿打下几颗毛茸茸的青蛋蛋,半是心疼半是埋怨地说:馋猫,看不把你牙给酸倒!

麦子在期盼中抽穗,扬花,终于泛黄,正值麦粒灌浆,闲不住的外婆夜晚不是在昏黄的油灯下熬夜纺线,就是摸黑去浇麦黄水,天亮时分才一身疲惫一身泥水的回来。
知了叫了。麦子熟了。放忙假了。杏儿黄里透红了。每逢这个时候,我会一日数次地爬上一搂粗细的杏树,迫不及待地填满肚皮,然后再把衣服口袋塞得鼓鼓囊囊。外婆多次规劝不敢贪吃,甚至让小姨监督,但我哪管得了许多,直到有一次吃得上吐下泻,好几天高烧才收敛了些时日,可很快又好了伤疤忘了疼。
十三岁那年,因麦黄杏还发生过一件至今想起仍然后怕的事情呢。
那个午后,艳阳似火,外婆顶着太阳割麦去了。小姨在家做饭。我死缠硬磨让小姨打开了后院的门锁,小姨看着我爬上高大的杏树,交代了几句小心、尽快下来、别让外婆知道的话便回屋去做饭。我站在树杈上,看着枝头上的杏儿已聊若星辰,再怎么伸手也摘不着,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突然间,我发现茂密的枝叶后仍有数十颗杏儿,看来只有爬到与邻居的界墙上才有可能触摸得到。闪念间,我付诸了大胆的实施。先沿着晃晃悠悠的树枝爬到墙上,然后颤惊惊地站起伸出手去,哪知身体重心顷刻失衡,一种条件反射使手忙脚乱的我下意识往墙体上趴,可没能成功,万幸的是,也就几秒钟,我晕乎乎手趴着墙体溜下了三米高的界墙,落地时正砸在邻家后院猪圈里晒太阳的老母猪身上,把那东西惊得吱吱乱窜,差点儿越圈而逃,惊魂未定的我已顾不了屁股疼痛,慌忙爬出猪圈,极力镇静心绪,从邻居大婶儿的堂屋穿过。
大婶不住地追问:”你啥时进去的,到我家后院干啥去了?咋弄成这个样子?”那边外婆割麦回来四处喊我不见回音,小姨跑到后院,任她望眼欲穿,就是不见人影。正焦急间,我一身灰头从大门外进来,小姨脸上写满了疑惑和诧异。

又是一年麦黄杏成熟时节,外婆病了,在外工作的我因百事缠身,井没在她去世前看一眼她老人家,这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外婆走时,舅舅把一搂粗细的杏树伐倒做了棺木。也许,勤劳了一辈子的外婆在九泉之下终于可以清闲的尝几枚一生也舍不得吃的麦黄杏了。
但是打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麦黄杏,可这酸甜甜的滋味和对外婆的思念在心底一压就是二十多个年头,浓得化也化不开。